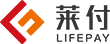中國銀聯的道路與步伐-迎戰移動互聯思維

“如果那山不向我們走來,我們就向大山走去。”
這句話是中國銀聯總裁時文朝在兩年半前的一場員工大會上說的。彼時,很多人、甚至包括銀聯自己人,都把當時的狀態比喻成在水流湍急處“裸泳”:一方面,享用了12年的特許經營權幾近殆盡,所謂“躺著賺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”;另一方面,是市場競爭白熱化,內外兩座“大山”壓頂。
內有移動互聯江湖酣戰。這種競爭甚至可以是非對等的,發改委的定價圈得住“線下”管不了“線上”,央行叫停二維碼支付后,最早擁有二維碼技術的銀聯停下了試點運用,但競爭者偷換“被掃”概念為“主掃”后,二維碼支付鋪天蓋地襲來,“滴”一聲把本該屬于銀聯卡的市場份額就掃去了線上——移動互聯支付巨頭們靠直連銀行達成閉環后的清算領地。
外有Visa、萬事達卡等老牌清算組織的虎視眈眈。這種競爭不止是在境外市場上對銀聯的崛起采用重重抵御(比如有某境外卡組織攢動部分商戶拒絕受理銀聯卡),也是在境內銀行卡清算市場全面開放前夜的備糧攻城,甚至不惜偷發直接可在境內刷人民幣的所謂“外卡”來搶跑。
銀聯選擇向這“兩座大山”邁步。從那一年開始,“愉見財經”也越來越多地在采訪中聽到銀聯人士說一個詞——
“主動求變。”
變與不變“取舍之間”
求變,變什么?
那一年有次采訪間歇,時文朝說起他接任銀聯以后的一個習慣,每天深夜辦公結束后,他都會在一張沙發椅上安靜沉思,既思考銀聯當下腳步,也思考這條路的發端——銀聯是誰?卡組織存在的根本價值是什么?如何分辨在支付生態里的圈層結構?
回歸基本面。這一系列問題的答案,決定了銀聯要怎么變。
變得大膽“創新”,為讓利潤好看故事好聽而無所不為?依托支付的擴張其實并不難,因支付天然接近現金流向,有數據有場景,具備靠撬動金融信用的支點去做“杠桿”的便利。如果要做,則從“匯”上溯至“存”“貸”,走向“T+N”的理財邏輯或“T-N”信用邏輯,有著65億張發卡和銀行業內合縱連橫關系網的銀聯,優勢得天獨厚。
事實上,時文朝的案頭也時常擺著此類創新經營提案。外界所見“老實保守”的銀聯,其實從不缺會開洞的大腦。
但是銀聯沒有變在這里。中國不缺一家利潤越頂實體經濟的金融機構,但缺一個“不爭”的卡組織、一個做基礎服務的真平臺——不與渠道爭入口、不與機構爭賬戶、不與收單爭場景。
大道至簡。既然是平臺,就該有邊界。
“既然你成了你,就應該心無旁騖,做好自己。”時文朝說。
那么如何“做好自己”,又該“變”在哪里呢?“要有產品、有規則、有品牌、有標準體系,有多元化的參與主體,有增進效率的規模經濟,有分工協作的平臺秩序,有因勢利導的順時運營。”這是銀聯向“愉見財經”給出的“好平臺”定義。
取舍之間。成為好平臺意味著放棄專業價值,轉而追求生態價值,而生態的價值在于“開放”和共同“進化”。
現在和未來的商業競爭已不再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競爭,而是企業生態之間的競爭;市場的邏輯不再是簡單的“誰強誰就贏”,而是誰進化得快,誰能找到更多的協同進化的伙伴,誰就能生存。因此,擴大生態范圍、推進協同進化是銀聯之“變”中的要務。
移動支付“雙管齊下”
銀聯的進化和開放,是市場以為銀聯在NFC(近場支付)一棵樹上吊著,但銀聯轉身就攜產業各方,在兩個多月前召開發布會推出了真正金融安全級別的銀聯標準“二維碼”。在移動支付領域,銀聯已然“雙管齊下”。
銀聯的進化和開放,是在兩個月前的那場二維碼產品發布會上,不止有監管坐鎮,不止有各大銀行、各大非銀支付的悉數到場,不止能用“云閃付”的統一口令協同Apple Pay、SamsungPay、Huawei Pay、Mi Pay齊步共贏,還有讓外界意想不到的京東、美團等互聯網巨頭高層出席。

老套的市場評論還在制造銀聯與互聯網企業的對立意象里刻舟求劍;而銀聯的開放,是早已伸出手拉上不同資質的產業各方,一道上路、協同進化。